 《日常對話》Small Talk
《日常對話》Small Talk
2016 │ 臺灣TW │ 彩色Color │ 88mins│普遍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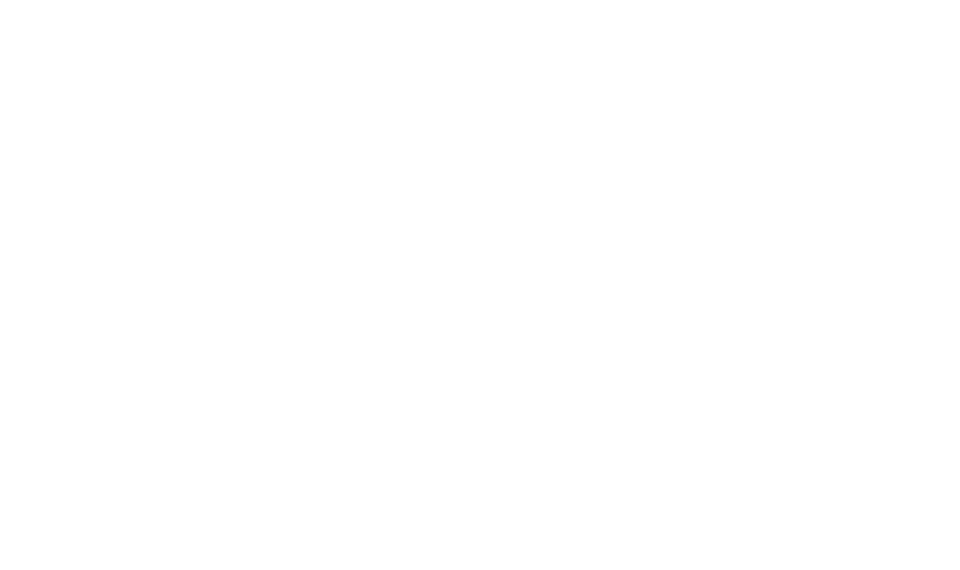
導演:黃惠偵
一個不應該被生出來的女兒,如何拿起攝影機,對著一個不該成為母親的母親,展開一場又一場的對話,只為了確認媽媽究竟愛不愛自己……。黃惠偵,小學肄業,在偶然機會接觸到了紀錄片,發現拿起攝影機、成為作者所能擁有的詮釋權,於是她存錢買攝影機,去社區大學上課,邊拍邊學。她積極社運活動,關注土地與移工議題,曾任職於NGO組織及紀錄片工會,三十多歲的某一天,她決定將過去十餘年所記錄的家庭影像整理出來,並拿起攝影機對準母親和自己,在家裡的餐桌上進行一場對話,最終剪輯成片長54分鐘的《我和我的T媽媽》和片長89分鐘的《日常對話》。
黃惠偵自承身上從小到大被貼了很多標籤,一個曾經遭受父親家暴、連小學都沒唸畢業的中輟生,有很長一段時間靠著被人輕視的牽亡歌陣維生,而這一切的源頭,都要指向她那當年帶著兩個幼女逃離家庭暴力的母親——她是從事牽亡工作的法師,同時也是情感豐沛結交過十數個女友的女同志。《我和我的T媽媽》幾乎有九成的片段皆出現在《日常對話》裡頭,但因為兩者在剪接和結構性上的不同,結果成為了情感、氣韻上不盡相同的兩部作品。如果《我和我的T媽媽》是黃惠偵寫給母親的一封影像信,那麼《日常對話》就是她做為紀錄者同時又身兼被攝者之女的自述和反思。
如果時間可以倒轉,人生可以重新選擇,T媽媽斬釘截鐵表示,自己絕對不會結婚,因為一個人比較自由。她承認,有時會怨恨必須要照顧兩個女兒;但她也承認,兩個女兒跟著她,多年來並不好過。上述對話出現在《日常對話》接近尾聲之際(但卻是《我和我的T媽媽》開場),或許可以將它視作《日常對話》的原點——一個不應該被生出來的女兒,如何拿起攝影機,對著一個不該成為母親的母親,展開一場又一場的對話,只為了確認媽媽究竟愛不愛自己。
黃惠偵不僅僅自己必須對著鏡頭開誠布公,還必須說動母親及多位至親面對鏡頭,和「拿著攝影機的自己」、和「不堪回首的過去」進行對話。其實《日常對話》和《我和我的T媽媽》兩個版本都極好,但《日常對話》格局更大,因為它除了講T媽媽,還藉著拍片之舉「重訪」了被封印在時光長河底層的家族陰影和個人傷痕。它不只要找回自己、不只要討論性別和性向、不只要確認母女關係的存在,它還質疑了揮之不去的父權幽靈。也因此,《日常對話》不僅在一派土俗中傳達出一股親暱感與混著土地和草根餘溫的詩意,更重要的是它勇於突破框架、格局恢宏。
《日常對話》並非影史首部由餐桌切入的家庭電影,2015年辭世的比利時導演香妲‧艾克曼(Chantal Akerman),在1975年的劇情片《珍妮德爾曼》(Jeanne Dielman, 23, quai du commerce, 1080 Bruxelles)中,餐桌即是作為女主角的日常展演,最必要的元素之一。然後在她的遺作,2015年的紀錄片《非家庭電影》(No Home Movie)裡頭,餐桌則是從單純的功能性擺設,進化成為母女情感拉扯、世代價值溝通的一個精神性場域。
從餐桌到居家空間,由家族歷史以至家族傷痛,如果說香妲‧艾克曼是以微觀的角度去辯證半個世紀的人類存在價值,那麼黃惠偵也不遑多讓,除了透過看似閑散的日常對話,讓觀眾逐漸習慣這樣一個敘事模式,藉以和影片後段那場「關鍵性的對話」形成反差,她甚至極具巧思地加入了歸鄉祭祖、重返祖厝這條路徑(對比黃惠偵和女兒、T媽媽共住的純女性空間)——且讓我們把家、祖、父、兄這些男性觀點串連起來,再對照T媽媽的兄長在電影中的發言,或許黃惠偵無意批判她的舅父等長輩,但作為這部女性電影中「少數的男性聲音」,《日常對話》非常微妙地,透過各式各樣(失格的、缺席的、存在的)父親形象,映照了台灣半世紀以來(以男性作為主導)的價值變遷。
本世紀初期,曾有多部以作者自身家族記憶為題材的台灣紀錄片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就在這個系譜差不多已經走到死胡同之際,黃惠偵的《日常對話》除了延續《我的回家作業》(曾文珍導演)、《雜菜記》和《黑晝記》(許慧如導演)等前輩作品中對於家庭和女性意識的反思,而且還在電影語言和視覺構圖上開創出新的局面。這是一部沒有絲毫妥協,也沒有故作溫情的鄉愿與簡化,極端台灣本色,同時又充滿普世情感的奇作。多數台灣紀錄片,只要達成上述其中一項就很難得,沒想到它竟然四者兼得
延伸閱讀
引導問題思考
- 《日常對話》是一部拍攝與母親、與女兒的對談語錄,除了表述及試圖釐清自己的成長疑惑外,也試著藉由攝影機打開更多的對話機會。看完影片,你對上述這樣的敘述是否同意,如果同意,你有觀察到什麼更細微的影片內容是支持這樣的敘述的嗎?如果不同意,說說看你看到了什麼?
- 開場畫面:拿著手機的手不斷的拿起放下手機,手的主人感覺有些無奈地被迫在等待什麼在思索什麼,鏡頭拉遠,看到是一位女子坐在沙發上。
「媽,以後我如果結婚你要怎麼辦?」
「我就自己一個人啊!」
接著鏡頭第三次切入到面部特寫逼近被攝者詢問更深入的問題:
「你自己一個人沒有人照顧」
「不用人照顧啦」(表情黯然)「我可以一個人四處走」
「不要錄了啦」看向鏡頭遠處「我要走了」
(鏡頭轉向黑幕的電視倒影,倒影中有著有些模糊的導演自己拿著攝影機拍著自己)以上的鏡頭切換對你來說是加強了情緒堆疊的效果還是切斷這樣的感覺?說說看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 - 《日常對話》一片中,導演使用了許多的成長照片、家庭錄像及自己與攝影師夥伴拍攝的影像進行影片的製作。你從這樣的素材及剪輯師的後期剪輯工作中看到了這樣一部片。你覺得有什麼素材是在這樣編輯的過程中可能被導演及剪輯師捨棄沒用的片段,你能想想並說說看為什麼這些素材能被拍到但不能用呢?
- 承續上題,如果妳也有這樣的機會用類似的素材製作屬於你自己的《日常對話》,你會想講些什麼故事?你會想對自己的母親/父親或是照顧你的人說些什麼話呢?
- 《日常對話》使用同樣的影片素材製作了《我和我的T媽媽》,導演試圖製作屬於電視版本的作品以及電影版本的作品。如果你看過了兩部作品,你能試圖比較看看兩部的異同嗎?如果你沒看過《我和我的T媽媽》,你能夠試圖想像看看,在電視播放的版本,你會做些什麼調整呢?
撰文:Ryan 鄭秉泓(高雄人,在東海大學和靜宜大學兼課,擔任高雄電影節短片策展人,當過金馬獎、金鐘獎、金穗獎、台北電影獎、長片輔導金、國藝會等評審,也是國藝會首屆「台灣藝文評論徵選專案」視聽媒體藝術類首獎兼特別獎得主。著作有《台灣電影愛與死》,編有《我深愛的雷奈、費里尼及其他》及《六個尋找電影的影評人》。影評文字散見《Fa電影欣賞》等報章雜誌,有時以英文名字Ryan發表評論)
問題設計:林佑運(台南藝術大學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碩士。於2015年起開始擔任影像教育扎根計畫之電影實作工作坊、觀影體驗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