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錢江衍派》Time Splits in the River
《錢江衍派》Time Splits in the River
2016 │ 臺灣 TW │ 彩色 Color │ 89 min │ 保護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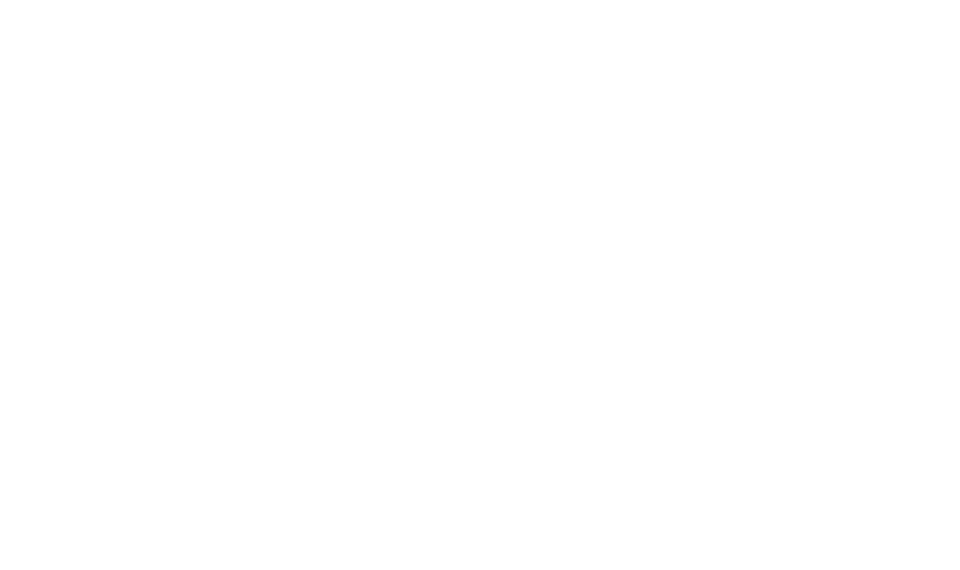
導演:王又平 WANG Yu-ping、李佳泓 LEE Chia-hung、黃奕捷 HUANG I-chieh、廖烜榛 LIAO Xuan-zhen
2018年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台灣競賽、華人紀錄片獎入圍
四名導演邀請了各自的父親一起拍一部電影,劇本改編自白色恐怖文學作家施明正的故事,四名父親則要演出八〇年代的異議分子。一開始,父親們先是試著演出他們想像中的異議分子,卻漸漸地在拍攝的過程中進入了自己的回憶,也在自己的故事和異議分子的故事交織後,展開對自我生命經驗的回顧反思。這項計畫的發想來自導演們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他們發現,家長雖然都肯定近代民主政治的發展,卻對於當今的社會運動有許多疑慮。此外,即便他們成長於社運蓬勃發展的八〇年代,但當年也都不曾親身參與其中。四名導演決定透過「拍電影」來和家人一同追溯這段過往,並藉此溝通彼此不同的想法。最後的電影則呈現了這段四個家庭之間互動、對話的過程。
第一部分:導讀與分析
片名指的是台灣民間常見的、三合院門口門楣上的「堂號」橫匾;「錢江衍派」代表了「施姓」大家族的源流與支派。這部紀錄片正是以「施明正」作為主角──他是一位天才型的藝術家 ,少年時代就是文藝青年,擅長繪畫、詩歌、小說。他有一位知名的弟弟:台灣黨外運動領袖、美麗島大審受刑人、在解嚴(1987)與民主化之後擔任過民進黨主席的「施明德」。
施明正在1962年被弟弟施明德的政治案件所牽連,以叛亂罪入獄五年。日後,施明正以一系列文體獨特、自傳色彩濃厚的政治小說,比如《指導官與我》、《渴死者》、《喝尿者》等,記述了這段親歷白色恐怖的惡夢、身陷政治牢獄的折騰,以及這些經歷深深烙印在他身上的嚴重創傷。施明正自述,戒嚴時代白色恐怖的監視、鎮壓、逮捕、審判、囚禁「捏破了他的膽子」,重重挫傷了他,使他從此成了一個「懦夫」與「廢人」,出獄之後只能開設國術館以推拿維生,寫一些帶有頹廢風格與失敗主義的小說。1988年,為了聲援因美麗島事件(1979)遭判無期徒刑、在牢中長期絕食抗議的弟弟施明德,施明正也在自己家裡絕食至死。
近三十年之後,四位年輕藝術家(王又平、李佳泓、黃奕捷、廖烜榛)在參與三一八運動(2014)後,沒有立即看見「島嶼天光」,反而是在運動過程中感到受傷、對運動本身產生了困惑,於是,他們想要透過藝術創作來重新開始思考「政治」、「革命」、和「民主」的意義。他們選擇的藝術創作方式非常特別:拿起攝影機,不只訪問了他們的四位父親,想知道他們在戒嚴時代的成長經驗,及他們對當前政治的看法,甚至,他們還依照施明正小說裡的描述,搭設了一間「施明正的家屋與書房」,讓這些父親「粉墨登場」,在這個舞台上或攝影棚內「扮演」施明正、施明雄(施明正另外一個弟弟)、鍾肇政(賞識與提攜施明正創作的一位台灣文學前輩作家)、以及《台灣文藝》(這是一本專門刊登台灣作家作品的文學刊物) 的社長,拍攝他們彼此拜訪、吃飯喝酒、談論文藝與政治的日常場景。
因此,《錢江衍派》這部紀錄片最後變得十分奇怪:除了一般紀錄片常見的「跟拍」或「訪談」片段外,居然還有「戲劇重演」的橋段。 一開始,觀眾會以為銀幕上是一部劇情片,一部以施明正和文藝友人作為主角、人物所在時空背景大約落在1980前後的劇情電影。不過,不久之後,觀眾忽然發現,劇中人物慢慢「露餡」了:好像酒不小心喝得太多,演員似乎忘了自己正在演戲、居然從劇本台詞「岔出去」、從劇情故事裡跑出來、開始談起他們自己親身經歷的事...。 但四位導演當時並沒有「喊卡」(讓爸爸們繼續說下去)、後來也沒有把這些露餡片段當作「NG」,而是把它們留下來,構成作品的一部分。
於是,《錢江衍派》最後成為一部有「紀錄片訪談」、「戲劇重演橋段」、以及「從劇情片不小心滑到紀錄片的『NG』片段」所組合起來的,非常奇特的「實驗紀錄片」。
第二部分:延伸問題
一、紀錄片意在「記錄真實」。但《錢江衍派》卻有大段的「戲劇重演」──「戲劇」和「表演」難道不是一種「人工製作」甚至是一種「虛構」嗎?你覺得紀錄片可以有戲劇成分呢?如果不行,那為何這部片可以被納入紀錄片的範疇呢?如果可以,表示這部紀錄片裡的戲劇成分也記錄了某一種真實──這是哪一種真實呢?
二、不只「戲劇重演」,《錢江衍派》裡還有幾段「實驗片擺拍」:選擇一個地點當作舞台,雖然沒有發生什麼事件或敘述什麼劇情,但人物在這舞台上,以設計過的動作或言語,表達一些抽象的狀態或概念。請你回想一下片中哪裡有這樣的片段,除了思考它到底表達了什麼之外,也同樣想一想:紀錄片裡的實驗電影成分,究竟和「記錄真實」有什麼樣的關係?
三、在戲劇重演的片段裡,導演群的四位父親粉墨登場。然而,顯而易見,這些爸爸們的演技不太好,因為他們根本不是專業演員、從未接受專業表演訓練,因而在片中時常出現口吃、台詞重複、肢體動作僵硬不協調、有時甚至表情或動作都略嫌浮誇......。既然這些父親演技欠佳、處處破綻,那為何導演群還要找他們來演戲呢?難道,這種卡卡的、破破的演技,這種「言語囁嚅」和「身體僵硬」,正是導演所要的(否則不會留在影片裡)?──為什麼導演群要這個?和全片的主題有什麼關聯?
四、為什麼導演群要透過爸爸們來重新思考政治?為什麼是爸爸們而不是媽媽們?政治只和爸爸有關而與媽媽無關嗎?──當然,你可以說,因為導演群要搬演的是「施明正」和「他的親兄弟」和「他的文藝哥兒們」之間的故事,無疑只好必須尋找男性來飾演。但這又引出另一個問題:為什麼導演群要透過「施明正這群男人」來思考政治呢?──你也許需要再搜尋一些關於施明正的資料,再想想施明正和這整部片想要傳達的主題間,有什麼樣的聯繫。
五、《錢江衍派》的後半段則是比較常見的紀錄片形式:訪談。(1)請你留意訪談片段,說說這些訪談片段給予你的感受是什麼?氣氛如何?提問與回答的雙方關係為何?親近還是疏遠?對等嗎?或者有什麼權力高低的張力嗎?(2)這些訪談片段裡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段?為什麼?(3)最後,在這些訪談片段裡,導演群有「入鏡」嗎?──導演選擇是否入鏡,都是考慮之後的決定,請你想一想「導演是否入鏡」代表了甚麼?「入鏡」或「不入鏡」的差別在哪裡?
六、訪談片段裡有一節值得注意:父母跟兒女討論他們合作(到一半)的影片。(1)在一部紀錄片裡討論紀錄片怎麼拍、拍得好不好,並不常見──它給予你什麼感受?為何導演們要大剌剌地在紀錄片裡討論紀錄片呢?(2) 在這段裡,父母對兒女說,「啊你們這樣拍,你們的教授看得懂啦,但像我這樣的一般觀眾看不懂。」(a)為什麼導演要留下這段話呢?(b)我們常聽到,在「劇情片」裡時常有「通俗商業片(或爽片)」和「(高深晦澀)藝術電影」的(粗略)區分。你覺得一部紀錄片必須讓一般觀眾看得懂嗎?然而,既然紀錄片是記錄真實世界的事物,那麼,置身在這個真實世界裡的觀眾,應該都看得懂才對啊?為何有些紀錄片會讓人看不懂呢?
七、在戲劇重演部分的一段裡,飾演施明正的那位父親,講述了施明正在獄中遭受刑求的故事。起初,這位非職業演員一如往常結結巴巴、言詞阻滯地背誦著台詞,然而,在某一刻之後,他忽然言詞流利、口若懸河起來,甚至興沖沖躺在桌上親身示範了刑求的細節,好像這位父親突然被施明正「附身」似的,身歷其境訴說著他當年的遭遇。──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如果你在看這部紀錄片之前或之後,另外讀了導演訪談,你可能會得知,這位父親的職業是刑警。──知道這個事實之後,你要怎麼看待和解讀這一段演出呢?
八、另有一位父親,在接近片尾的時候,朗讀了一段英文。這一場很特別:父親坐在他的老母親身旁(也就是導演之一的阿嬤),對著鏡頭朗讀一段英語文章,內容是對兒女的祝福和期許;同時,畫面另一邊的阿嬤,在藤椅上扭來扭去,不知道她兒子到底在旁邊碎碎唸甚麼(她完全不懂英語),一副不理解也不耐煩的模樣,甚至時不時用台語和她另一個兒子(導演之一的叔叔)閒聊。這場戲無疑是經過設計的:刻意讓「英語父親」和「台語阿嬤」並置對照──為什麼導演要這樣設計呢?為什麼是「英語」而不是阿嬤也極可能不熟或不懂的「國語」或「另一種外語」呢?為什麼父親要以英語對著兒子陳述他的祝福和期許呢?
九、片中有位父親經營了一家小水族館,這間水族館成了片中重要的場景之一,而且片尾正是以水族箱裡色彩斑斕的金魚特寫鏡頭結束了整部片。(1)片中這位父親在這間小水族館裡述說了他的生活日常,請回想他說了什麼、這段話給予你什麼感受?以及這段話和這部紀錄片的主題間的關係是什麼?(2)為什麼導演群決定以水族箱裡的金魚特寫作為全片的結尾呢?
十、這部紀錄片的導演不只一位,而是四位年輕藝術家。(1)雖然拍電影(無論劇情片或紀錄片)是一件團隊工作,但導演往往只有一位,由導演拍板決定一部電影的最後樣貌(拍片過程和後製過程有一連串的決定要做,比如留下或捨棄哪些鏡頭,比如怎麼剪接排列鏡頭、組織全片結構)──為何這部紀錄片卻有四位導演呢?(2)這四位年輕人並不是電影科系出身、而是來自藝術學院,他們傾向稱呼和定位自己為「藝術家」而非「導演」──電影難道也是一種藝術嗎?「藝術家」和「導演」的差別在哪裡?「電影」和「藝術作品」的差別又在哪裡呢?
撰文:陳平浩
臺大外文系、中央大學英美文學所畢業。曾任《放映週報》專欄作者和採訪編輯,影評另見《破報》、《電影欣賞》、《紀工報》等。長年寫作一種介於「影評」和「論文」之間、篇幅冗長的電影文章。近年擔任巡迴電影學校講師,透過投影與吹奏,引領高中生進入電影的迷人聲光世界。